蒐羅與財經、理財相關書籍內容介紹及書摘,協助讀者快速閱讀書籍精彩內容。
走上破產這條路的人,全因好吃懶做、遊手好閒?
在我對破產新法研究越來越深入後,總會不停繞回到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人會破產?我找不到有說服力的答案。當時的年輕法律系教授幾乎都是理論派,他們的所有文章和書籍都以理論為基礎,但是理論無法提供可靠的答案讓大家參考,也無法解釋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錯。我緊緊抓著「申請破產的人和我們不同,其他人很安全」的信念,以為在尋求為什麼有人要申請破產的答案時會見到一堆騙子和好吃懶做的人。
幸運的是,我在研究剛起步時就遇到兩個優秀的夥伴:一個是泰麗.蘇立文(Terry Sullivan),她剛拿到博士學位,被視為社會學院的明日之星(泰麗後來成了維吉尼亞大學的首任女校長,事業非常成功);另一個是已經有十一年律師經驗的破產法專家杰.威斯布魯克(Jay Westbrook,現在他也是成就非凡,不但是個著名的破產法學者,還是公認的國際商事法專家)。當時,我們只是三個年輕的法學教授,興奮地想做出幾乎沒有任何法學專家做過的研究──我們決定蒐集破產家庭的資料。
泰麗領著我們規畫抽樣數量、列出我們想取得的資料清單、影印個案、記錄數字,開始建立資料庫。在此之前,我從未參與過這種謹慎規畫、系統性取得資料的專案。我相信我們蒐集到的資料能勾勒出申請破產者的輪廓,然而漫長的取樣過程就像是在鑲嵌一幅巨型馬賽克壁畫,只能一次一小片地往上貼。
在資料蒐集期間,我曾到聖安東尼奧的法庭旁聽。這座老舊的法庭牆面都是木鑲板,正值盛夏,冷氣涼到可以在一分鐘內把你凍成冰棒。那個年代的人仍必須親自到法官面前陳述,才能得到債務免除的裁決(現在這個程序已簡化成郵寄通知)。我坐在法院後方的長椅上凍得發抖。
法官座位比房間裡的任何座位都高,不過我幾乎沒注意他,而他也完全沒有看我一眼。我專注地看著在法庭裡進進出出的人。我猜我之前對破產人的刻板印象太過深刻,以為會看到一群衣衫襤褸、賊頭鼠眼或邋遢猥瑣的人,但是他們看起來和正常人沒兩樣,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站在法官面前的人,膚色、體型、年齡各不相同。好幾個男人穿著明顯不合身的西裝,其中兩三個還戴上德州領結,看得出來幾乎每個人都為了上法院特地打扮過。他們像是一群要到教會做禮拜的好人。一對老夫婦手牽手,小心地走下通道,在前頭找位子坐下。一個少婦輕輕晃動鑰匙串逗著膝上的嬰兒。所有的人都很安靜,不是一言不發,就是壓低聲音交談。律師們(至少我以為他們是律師)就像牧羊犬一樣,把人群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
我沒有在那裡待很久。我覺得自己彷彿認識法庭裡的每一個人,讓我難過到迫不及待地想離開。那種感覺像目睹了一場車禍,而傷亡者居然是你認識的人。
你以為自己很安全,但其實你很脆弱
我們後來蒐集到的資料,證實了我在聖安東尼奧法院的觀察:那些在法官面前請求免除債務的人,曾經都是不折不扣的中產階級。他們上過大學,有過好工作、結了婚、買了房子,但是現在卻一敗塗地,站在法官和全世界面前,準備放棄他們擁有的一切,只為了可以在討債公司的壓迫下喘一口氣。
資料蒐集得越多,看到的故事越可怕。全美各地申請破產的人幾乎絕大多數都是遇上難關的正常家庭,聖安東尼奧也不例外。一段時間後,我們發現將近九成的人申請破產不外乎三個原因:失去工作、健康問題和家庭破碎(通常是離婚,但也有少數是配偶死亡)。當這些家庭走進破產法庭時,基本上都已經走投無路了。在爸爸被辭退或是媽媽罹癌後,無法擺脫經濟困境超過一年或更久。他們沒有存款、沒有退休金,車子或房子全被貸款壓得死死的。許多人積欠信用卡債的金額超過一年以上的收入,欠下這麼多錢,即使一輩子都不再買東西,即使爸爸明天就回原來的公司上班,媽媽立刻奇蹟似痊癒,像山一樣高的負債只會在罰金和循環利息的助長下每隔幾年就翻一倍。等他們來到破產法庭時已經債台高築,放棄一切換來無債一身輕,看起來比現狀好太多了,絕對值得吞下個人尊嚴,厚著臉皮尷尬的申請破產。
然而糟糕的是,申請破產的家庭數目不斷攀升。我和夥伴們在一九八○年代早期開始蒐集資料時,每年有二十五萬戶家庭申請破產。沒錯,經濟衰退確實動搖了國家經濟根本,讓許多家庭陷入絕境,但是在經濟復甦之後,申請破產的家庭數目卻出乎意料的增加了一倍。突然間,報章雜誌、電視新聞出現了許多評論,指責美國人不辨是非,買一堆不需要的東西,卻在繳不起帳單時躲藏逃走。銀行大聲抱怨許多人不付信用卡帳單,他們大量使用「遊手好閒、欠債不還」一類的語彙來抹黑破產的人,彷彿申請破產的人不只是在經濟上跌了一跤,還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部分的我想繼續相信這個「遊手好閒」版的故事,因為這會讓我覺得心安,但是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逐漸看到了這些人的真面貌。
在我們的研究裡,有一項要求是請破產人以自己的話去解釋為什麼他們會申請破產。我以為大多數的人會為自己辯解,講一些美化自己或為自己脫罪的故事。
我還記得自己坐下來拿起第一疊問卷開始讀時,眼睛已經累到快閉上了。
接著,上頭寫的答覆卻像有人結實地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紙上充滿了自我厭惡的情緒,有個男人只以三個字來解釋他為什麼會破產:
蠢
蠢
蠢
寫到他們的生活時,許多人責怪自己不該向銀行借了他們其實沒有搞懂的貸款。他們責怪自己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工作沒有保障。他們責怪自己誤信居心叵測的丈夫或紅杏出牆的太太。顯而易見的,我看到的大多數人都將破產視為個人的巨大失敗,代表他們是徹頭徹尾的輸家。
有些人把他們的故事哀傷地說給我們聽,比如孩子病死、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三十三年後被無情裁員;而有些人則一語道破赤裸裸的現實:
老婆罹癌死亡,保險給付後仍需自付六萬五千美元。
找不到全職工作。打五份工才能付得出房租、水電、電話費、食物和保險帳單。
他們以為自己很安全,不論工作、健康或婚姻都不用掛慮,但天不從人願。
我的手指滑過其中一張問卷,看著一個女人努力解釋為什麼她的人生會變成一場大災難。這裡或那裡拐個彎,她的人生或許會完全不同。
離婚、不幸福的再婚、生了重病、找不到工作。這裡那裡拐個彎,或許我的人生也會完全不一樣。
書籍簡介_不大好笑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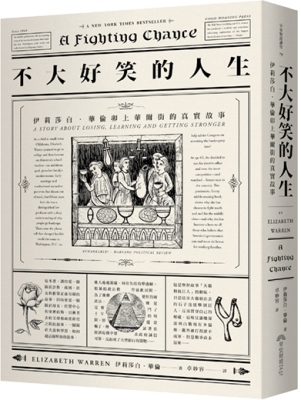
不大好笑的人生─伊莉莎白.華倫卯上華爾街的真實故事
原文書名:A FIGHTING CHANCE:A STORY ABOUT LOSING,LEARNING AND GETTING STRONG
作者:伊莉莎白.華倫
譯者:卓妙容
出版社:早安財經
出版日期:2018年06月27日
中產階級啊,不是你存不到錢,是他們早就設下陷阱!
我叫伊莉莎白・華倫。我是個妻子、母親,外婆。在大半人生裡,我是個老師,現在是美國參議員。
這是一本關於我的故事,一個手忙腳亂、麻煩不斷、講笑話不好笑、烤麵包卻烤箱著火的故事,一個關於早婚、離婚、再婚的故事,一個關於母女之間、安親班和狗兒之間、年邁父母和頑皮孫兒之間的故事。
但這也是關於你的故事,一個金融業者如何假理財真詐欺、中產階級血汗錢如何遭到吸乾的故事。如果你以為自己的存款很安全,如果你以為政府會替你把關,以為倒楣的噩夢不會降臨到你身上,等你看完我書中的故事,你一定會一身冷汗地笑不出來。
作者介紹
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
麻州資深參議員。曾任哈佛法學院教授,也是經濟議題專家。美國民眾普遍認為她是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催生者。她以歐巴馬總統助理的頭銜幫助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她也擔任過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國會五人監督小組的主席,以及國會破產法審查委員會的資深顧問。擁有兩個孩子、三個外孫,現在和丈夫布魯斯・曼恩住在麻州劍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