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史蒂芬妮出生於社會底層,努力成為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畢業後竟墜入學貸地獄,只好展開她從未想過的職涯:幫紐約上東區富豪帶小孩。但金錢能買到的東西、階級的現實、僱主家的精緻教養,都刺痛著童年充滿陰影的史蒂芬妮。她也同時看見,即使是有錢人家裡高學歷、高成就的媽媽,也和普通家庭的媽媽一樣,面對著過多的要求、失衡的親職分工。這一切讓她陷入了迷惘:擁有金錢,就等於擁有幸福嗎?
我在學校外面排隊等著接小孩,夾在好萊塢傳奇巨星茱兒.芭莉摩和前總統小布希的親戚中間,前面的前面排著喜劇演員史蒂夫.馬丁和他太太,因為距離實在太近,這對名人夫妻檔聊了什麼,我全都聽得一清二楚,但實在聽得很沒勁,我已經看過馬丁和他太太好幾次,早就見怪不怪。馬丁看起來雖然有一點點冷傲,但感覺人很好,他太太則長得超級像劇作家蒂娜.菲,像到不可思議,有一次,我偷聽到其他貴婦竊竊私語,彷彿說人家長得像蒂娜.菲會得罪人,但我可不這麼想。蒂娜.菲是開路先鋒、是國寶,馬丁都72歲了,跟哈利波特戴同款眼鏡,能娶到像蒂娜.菲的太太,簡直是賺到,而我就站在他幾步之後,顯然也是賺到了。
東六十四街的這一段停滿了黑頭車,大多是凱迪拉克和雪佛蘭休旅車,兩端街口分別是公園大道和麥迪遜大道,貴婦們肩背愛馬仕包包,身上的行頭至少30萬起跳,手上的戒指光彩奪目—精緻的美甲,大大的寶石。紐約市這天沒什麼活動,就只是個尋常的星期二下午,但對於聖公會幼稚園外頭這群花枝招展的貴婦來說,過日子就像在走秀。【*編按:為方便讀者理解,本書中所有金額數字,皆換算為臺幣呈現。】
這群貴婦雖然未必有出眾的容貌,但是無所謂,就算運氣稍差、老天不賞「臉」,多費心打扮打扮就得了,有的足蹬Jimmy Choo高跟鞋在街上走,看得我目瞪口呆,有的穿著皮褲,也不看看時間(拜託,現在是平日下午3點耶),而且,貴婦好像都對陽光過敏,清一色戴著粗框墨鏡,藏住眼睛。有位貴婦提著香奈兒購物袋,我假裝不經意往裡頭看了看,不管袋子裡面裝了什麼,我都想要。這些貴婦隨便一枚鑽石耳環的錢,都比我所有戶頭的財產加起來還多。(中略)
前面傳來一陣笑聲,一群保母擠在隊伍最前頭,我很好奇是在笑什麼,對啦我就是幼稚,死拚活拚也想要拚進保母的小圈圈。過去幾個星期,無論我跟誰對到眼、對誰微笑、找誰攀談,通通都被無視。我雖然考慮混進保母的圈子,但立刻察覺:比起愛麗跟我打交道的機率,保母歡迎我加入的機率也沒有比較高,一邊是典型的紐約上東區貴婦團,一邊是典型的紐約上東區保母團,我無論去哪邊都格格不入,最後的下場就是半個朋友都沒有。
3點半。身高195的保全打開厚重的實木校門,接著站在校門旁邊,一邊讓我們進入幼稚園,一邊小心翼翼打量所有人,像極了我週末在米特帕金區看到的夜店圍事,只差保全沒有攔下我不讓我進去,還有就是來接小孩的人大多很清醒,而這位幼稚園保全善盡職責、慎重其事,畢竟他保護的可是全美國身價最高的寶寶。
一開始我覺得很扯。頭幾次來接露比放學,覺得這裡的保安實在高到離譜,但普通人家的小孩是進不了這所幼稚園的,除非爸媽是政客、名人、體壇明星,這種人家的小孩享有的殊榮,我至今還是搞不太懂。走上通往中班教室的臺階,我努力回想自己第一天上幼稚園的情景,終於,我想起來了:我根本沒上過幼稚園。
露比蹦蹦跳跳到我身邊,一碰面就問我能不能去公園玩。我們一面走下臺階,她一面細數最愛哪些遊戲設施,我跟在後面靜靜地聽。走出校門,我牽起露比的手,沿著第五大道走過八個街口,一路上都是整潔明亮的高樓大廈,腳下的人行道一塵不染,紐約市髒得出名,唯獨第五大道乾乾淨淨,光著腳走路也不用怕。
10月初的日子。距離我大學畢業已經過了半年,這是我住進紐約的第四個月,我一邊送露比回家一邊想:能找到這份工作真是太幸運了。
我住的公寓在東哈林區,雖然治安堪慮,但室友萊菈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從高中就玩在一塊,每到週末就窩在我外婆家的破沙發上追《唐頓莊園》,畢業之後到處造訪紐約最潮的夜店。在我看來,我真的是鵬程萬里了。
搬進紐約兩個月後,聯邦政府開始通知我還學貸,每個星期寄電子郵件來提醒我有這麼個大包袱。我的學貸負擔超級重——買兩部新出廠的BMW還有找。18歲那年,我申請了7位數的學貸,當時我經手的錢最多就幾萬塊,對錢沒概念,自然覺得不痛不癢。
我卯起來想找一份既能養活自己又能按時還學貸的工作,所有娛樂圈能面試的崗位,我幾乎都面試了一輪,多虧我大學還主修電影和電視創作,出了社會一點用處也沒有。
我整個大四都在獅門影業一位王牌製片底下實習,成天讀著源源不絕的劇本、幫劇本打成績,工作起來超級帶勁,覺得自己天生就是做這一行的料。畢業後,我來到紐約接受人生第一場面試,才知道娛樂圈基層的起薪比大多數的速食店還要低。
好萊塢是用錢堆出來的,那些錢都到哪裡去了?我在猜:如果李奧納多拿了十億片酬,幕後人員能分的錢大概少得可憐,反正資深助導說怎麼分,大家也只能摸摸鼻子。
我決定遷就職場,應徵公關公司的臨時工,一方面薪水比較高——雖然也高不到哪裡去,但應該夠我生活——二方面多多少少能發揮創意(但未必是我原本追求的那種創意)。
上班沒多久,學貸冒出頭來打招呼,這下就算是公關公司的薪水也不夠支應。每個月4萬7的薪水,只夠我吃東西、付房租、搭地鐵,還有最重要的,修眉。學貸通知一寄來,我立刻領悟:就算我不吃不喝、走路上班、自己修眉,攢下來的錢還不夠還學貸的一半。我快速心算了一下:每個月至少要賺8萬多!嚇死人了!
後來,我發現只要替有錢人工作,就可以不用為職涯起步的低薪發愁,因此,我立刻抓住機會。
帶小孩是我想都沒想過的工作,但比起面子,活下去更重要,所以……本來還是社會新鮮人的我,就這麼當起了寶寶的私人助理。
走到第九個街口,露比在東七十三街停下來說想買冰淇淋。
「什麼口味?」我問。
「薄荷巧克力。」
露比每次都選一樣的口味,但薄荷巧克力是我最不喜歡的。露比媽不太反對點心,總是會留現金給我,露比隨時想吃什麼都能買。冰淇淋在我小時候是稀罕的奢侈,就跟遠足一樣沒辦法常常有,但還是有例外。
我爸跟我媽分居的那陣子,他在一間工廠當技師,星期五輪到他來照顧我和我妹,恰好星期五也是發工資的日子。
「一人150塊。」爸爸說著帶我們走進沃爾瑪大賣場,那感覺就像一生一次的失心瘋大血拚,我通常都買些沒用的東西,像是美甲貼片、1袋15支的ChapStick護唇膏,最後再走去冰淇淋店,這時爸爸會掏出信封袋,裡頭裝著他拿支票去銀行領的現金。
但露比跟我不一樣,只要天氣不冷,她幾乎天天都有冰淇淋吃。這天放學後,我們在中央公園的草地上跑跑跳跳,接著坐在船屋餐廳看遊客划船,就這樣度過了好幾個小時。紐約對我來說還很新鮮,我看著遊客到處拍照,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已經不是過客。我帶露比從中央公園走回家,路程雖然短,但露比卻看見冰淇淋車,立刻興奮大叫。我滿手抓著餐巾紙,露比在我眼前蹦蹦跳跳,愈蹦愈遠,忽然間,我的手機震了一下,我一邊從屁股口袋抽出手機一邊喊:「露比,等一下!」
我瞥了一眼螢幕,看見我媽傳訊息來,雖然很煩,但也只能點開,如果我遲遲不讀不回,我媽一定會一直傳一直傳,她這人什麼都不懂,就是執著。
「妳爸把浴室拆了要重新裝潢,但我們沒錢買新馬桶,可以跟妳借6千5嗎?去外面上好麻煩。」
我嘆了口氣,把手機塞回口袋,門房幫露比和我開了門,我們走進照明昏暗的門廳,一邊等電梯,我一邊看著搖曳的燭光照著一幅鑲金框的畫,畫本身不怎麼樣,但裱框裱得很漂亮,又給擺進了高檔的房子裡。這幅畫跟我,真像。
我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都稱得上歹竹出好筍,費盡千辛萬苦才爬出混亂的童年。我媽的簡訊雖然短短幾個字,卻打開了我的記憶水閘,被我鎖住的往事如洩洪般湧現,我想起了小時候、想起了自己的出身,想當年我爸媽都還太年輕,成熟不足、責任有餘,一家人住在破爛的公寓裡,沒有保母,沒有陪玩姊姊,外婆一邊照顧我,一邊照顧自己老邁的父親。我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從平價百貨Kmart買的,而且還是分期付款,衣服和鞋子塵封在貨架上,等到付清才能取貨。我們全家(包括我)都很愛尖叫,罵髒話從不嘴軟,我才3歲就對我媽比中指,而且有圖有真相。
帶著露比,我吃的是精品超市的頂級老饕三明治,搭的是Uber,逛的是紐約知名的博物館和美術館。我的童年是日復一日的債主上門,寵物怎麼養都活不過幾個月,三餐分量有限,我妹和我常常餓著肚子上床睡覺。
這樣的我,竟然可以待在這樣的地方——做這樣的工作,光想到還是覺得腦筋打結。
電梯咻一下來到6樓,露比一進門就大喊媽咪,紗夏立刻從大廳另一頭趕來,精緻的拖鞋走起路來沒半點聲響。
「媽咪來嘍。」紗夏對露比說。
紗夏先將露比擁入懷裡,再問露比今天過得怎麼樣,一舉一動都散發著滿滿的愛意。老是目睹別人家最親密的時刻,感覺好奇怪,而且總讓我渴望那些我人生中根本不曾存在的親密時刻。我把這念頭甩開,並且說服自己:反正這麼溫柔的交流我根本無福消受。
在上東區的貴婦中,紗夏絕對是奇葩,長得美,頭腦好,才35歲就有錢到爆,爸爸媽媽都是耶魯大學畢業,紗夏也是,紗夏的老公也是,她那隻小拖把似的哈瓦那犬如果去考,我保證也一定會錄取。紗夏雖然不用上班,但任職的募款委員會比我知道的募款委員會還要多,這算是上東區特有現象:富家女讀了十幾年的書,考進普林斯頓、史丹佛等名校,取得學歷後卻不用找工作;對這些富家女來說,受教育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彰顯身分地位。職業婦女在上東區很罕見,而且通常不受青睞,在貴婦圈中敬陪末座。
紗夏的學經歷加上家族的名氣,讓她在社交圈如魚得水,別人想學也學不來,但紗夏總是會客客氣氣跟我打招呼(我則眼睜睜看著其他貴婦說三道四),再將注意力快速轉移到大寶、二寶身上。
究竟「好」媽媽是什麼意思?自從我開始帶小孩之後,這個問題就一直在我心頭打轉,看來女人樣樣都能兼顧的想法,終究——只是想法。我每天都會遇見形形色色的媽媽:有的是女強人,位高權重,年薪驚人,有的是怪獸家長,對小寶寶的餵奶時間「分秒必爭」。可是,我還是沒找到養出天使寶寶的祕訣,也還是沒遇到完美的媽媽。
紗夏近乎完美:她熱衷當媽媽,全心全意無私投入,唯一有問題的地方大概就是僱用我——22歲、徬徨失措、連自己都討厭自己——來幫她帶小孩。
我幫露比把書包裡的東西拿出來,拿到一半突然決定借錢給我爸媽,一來我爸會還我,二來這種請託不能拒絕,我已經搬出老家了,新馬桶買了我也用不到,想到這裡就覺得很安慰,因為老家的浴室連個洗手乳都沒有,而且毛巾全是破洞。
如果我需要上廁所,可以使用第五大道的浴室,裡頭是鏡面牆和黑色大理石,備有奢華護手霜,還有無可挑剔的厄瓜多女傭,她把馬桶打掃得乾乾淨淨,將捲筒衛生紙的第一段摺成小三角形。
延伸閱讀
底層女孩在億萬豪宅當保母的啟示:財富教會我兩件事,一是友情比錢財更有價值,二是尊嚴無價
透過不刻意炫耀來炫耀?為什麼有錢人愛穿牛仔褲和T恤,都戴這2種錶?
書籍簡介_我在億萬豪宅當保母:一個底層女孩在頂層社會的窺奇與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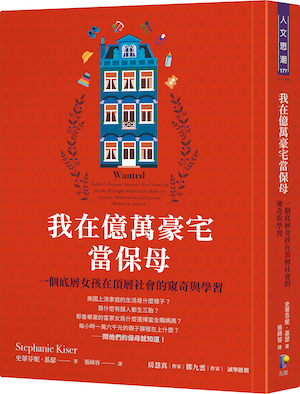
作者:史蒂芬妮‧基瑟(Stephanie Kiser)
譯者:張綺容
出版社:先覺
出版日期:2025/02/01
作者簡介_史蒂芬妮‧基瑟 Stephanie Kiser
史蒂芬妮原本是保母,住在紐約市。她來自羅德島州的北普羅維敦斯,後來搬到波士頓就讀愛默生學院,主修電影和電視創作。轉換職涯前,史蒂芬妮為曼哈頓的頂級富豪帶了七年的小孩。目前,她是紐約市一家廣告科技公司工程團隊的資深行政助理。她雖然不是工程師,對寫程式一知半解,但幸好並不影響她成為出色的行政助理。
史蒂芬妮目前住在阿斯托里亞,室友是一隻查理斯王騎士犬,名叫漢堡包.柯林頓。《我在億萬豪宅當保母:一個底層女孩在頂層社會的窺奇與學習》是她的第一本書。
譯者簡介_張綺容
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現任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著有《譯氣風發的高雄煉油廠》,合著有《英中筆譯》系列二冊、《翻譯進修講堂》、《英譯中基礎練習》,譯作包括《史丹佛大學創意寫作課》《傲慢與偏見》《大亨小傳》《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等二十餘本書。